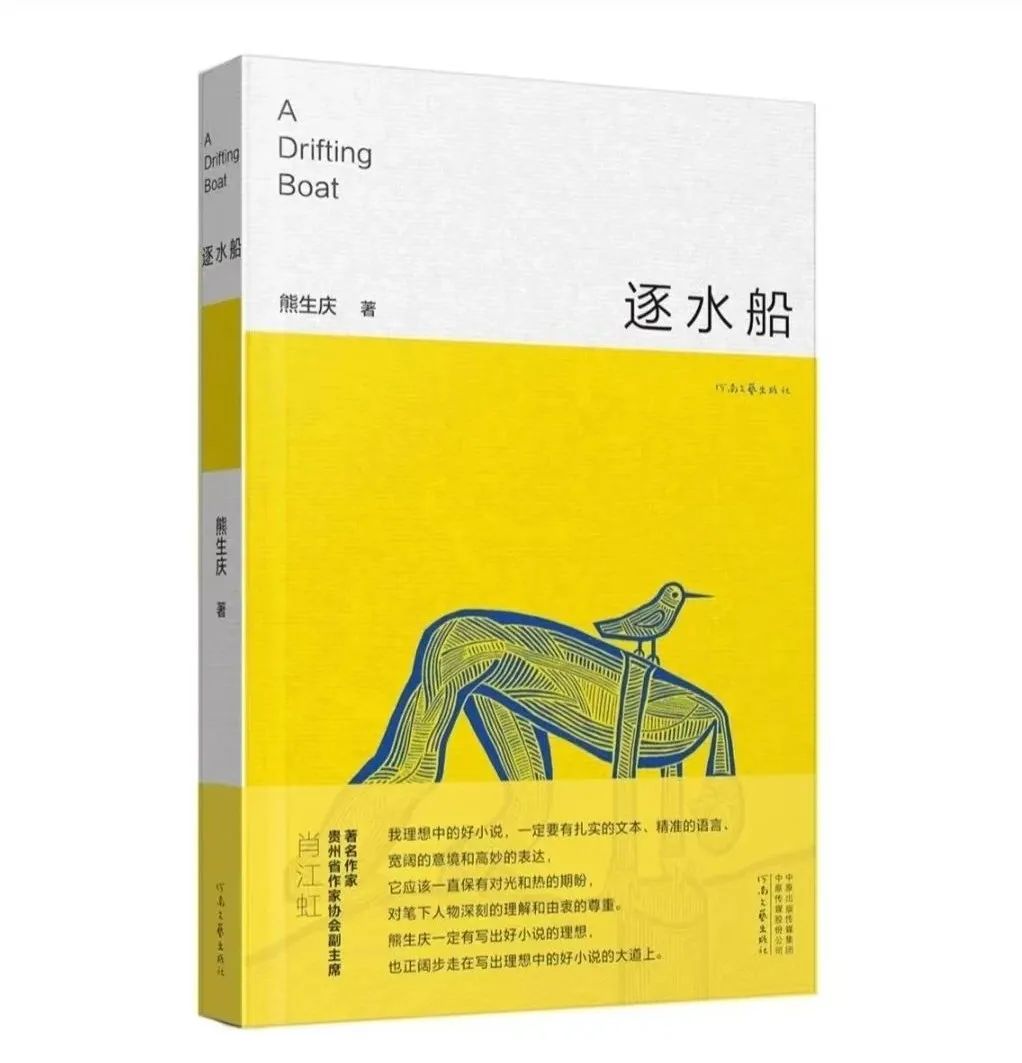贵州青年作家熊生庆小说集《逐水船》出版发行
作者: 来源:贵州省作协 动静贵州 发布日期: 2025-07-11 14:12:15
近日,贵州90后作家、贵阳市作协副主席熊生庆的小说集《逐水船》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熊生庆小说集《逐水船》封面
《逐水船》以我省“三线建设”旧厂区为地理背景,呈现了“苗刀”传人、孀居女人、空巢老人、工人等小人物的生命状态。小说中的许多人物经历失败,生活落魄,但他们身上仍有生生不息的生存韧性、充沛的生命活力。作家着力表现小人物身上淋漓的元气与旺盛的生命力,也直面他们在惨淡人生中的挣扎与沉浮。小说语言准确,文学质地细腻绵密,塑造的各色人物既有一定的传奇性,又能让读者感受共通的时代经验、人生经验。

《逐水船》书影
《逐水船》收录的10篇小说,此前已先后在《山花》《青年文学》《福建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南风》等刊物发表,部分作品还被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思南文学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选载。作品发表后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,李晁、王辰龙、王贺霖等先后对其作品进行评论。著名作家肖江虹、《青年文学》主编张菁张菁为该书作了推介。
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鲁迅文学奖获奖者肖江虹在推介中说:“我理想中的好小说,一定要有扎实的文本,精准的语言,宽阔的意境和高妙的表达,它应该一直保有对光和热的期盼,对笔下人物深刻的理解和由衷的尊重。熊生庆一定有写出好小说的理想,也正阔步走在写出理想中的好小说的大道上。”
《青年文学》主编张菁则认为:“‘逐水船’作为命运的符号意象,承载着完整且令人信服的表达。女主人公的命运几乎与风浪同频,宁静安稳往往只是片刻,但她面对苦难时依然守护着内心的光亮。”

熊生庆近照
《逐水船》出版后,入围了“探照灯好书”6月原创小说书单,目前淘宝、京东、当当等各大网络平台有售。
《逐水船》自序
熊生庆
2019年底,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考量,我决定放弃诗歌写作,全身心投入到小说上来。那是我诗歌写作的第六个年头。我深知自己的局限,依旧热爱,但不得不放弃。我用六年时间,来证明自己不适合干这事。
为什么转向小说,如今想来颇觉可笑。在一篇创作谈里,我曾说过,是为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。说了等于没说。坦白讲,对小说的喜欢是前提,此外还有个诱因:当时集中读了批青年作家的小说,心想这活儿我也能干。写了两年,发现不是那么回事。好在也慢慢摸到些门道,于是暗下决心,先写个三五十万字,行不行,再说。这个意义上讲,这本集子对我有特殊意义。我无比珍视她,尽管她有诸多不足。
收录的十篇小说,大多写于2022至2023年,那是个特殊的时段,不用我赘述。加上那会儿我刚从县城调到贵阳,工作性质变了,突然有了大把的时间,之前没得到满足的表达欲,终于可以尽情释放。我边读边写,平均每周读一到两本书,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了近四千字。那段时间写的东西,多半都成了废稿,但废稿也是建立写作信心的一种途径。我写,固我在。
我五岁上学,天性调皮,经常被父亲收拾。每次犯了错,父亲都会罚我蹲马步,边蹲马步边让我背书。要是背得好,可以少吃点苦头。一段时间后,我找到了应对父亲的方式。课文背不了几篇,没关系,自己编。父亲不识字,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。只要勉强编得像那么回事,就能蒙混过去。我想,这应该是我虚构的开始。那时候,我还没学会虚构这个词,但却实实在在体会到了虚构带来的好处。原来它可以是我抗争的武器。
虚构是会上瘾的,这种东西像种子一样,给它合适的阳光、雨水和土壤,便会慢慢生根发芽。意识到这颗种子的存在,并有意识地呵护、培育它,是上大学以后的事,那时我想,命运一定对我另有安排。我告诉自己,要走该走的路,经受该经受的,让那种子长成一片内心的风景。就这么走过来了,直到现在。
现在,虚构是我认识和理解人,人的命运,以及这个世界的方式,是我打开一扇又一扇未知之门的钥匙,是我无比确信却又羞于说出口的志业所在,是在这尘世之中修持自身的法门。
现在,这本集子就要与大家见面了。写这篇短序之前,我又将书稿过了一遍,本打算谈谈创作缘起,以及自己对小说的理解,冷静想,没有必要,小说写完,就跟这些东西没关系了。一个写作者谈论自己的写作是尴尬的,作品就在那儿。那么,请允许我怀着忐忑与惶恐,对我的家人,对这一路走来给予我温暖和帮助的师友们,和促成此书出版的老师们表示诚挚的谢意。文学的辉光必将一直照亮我们,也照亮恰好读到这本书的你。
评论
好小说的理想和理想的好小说
肖江虹
生庆九零后,第一次读他的小说,文本里弥漫着的沉郁和繁博,与其代际实在相去甚远。可能和早先写诗有关,转入小说创作后,语言呈现出难得的精准和简洁。少用修辞,直呈真相,文本洒脱爽利。
难得的是,在“技”的基础上,生庆对于文学“道”的层面也有属于自己鲜明的认知。他的小说作品,从选材,切口,文本的内涵和外溢,到形而上的审美和哲思,都有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。他没有圄于个体经验的书写,而是放眼四顾,上下打量,自信坚定地“讲述别人的故事”,这一点,在他《喝早酒的人》和《逐水船》两个小说中有非常出色的表现。
《喝早酒的人》关乎的其实是一种撕裂后的疼痛感。被撕裂的当然不仅仅是生活方式,还有人和人在朝夕面对中建立起来的情感调值,这种内在调值的稀释和消散,甚至比现实的凋敝和没落更让人唏嘘。喝早酒看起来是一种日常时态,本质其实是人对于某种关系和情感的体认,并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去维系和筑牢这种关系和情感。人不在了,但架子上属于那个人的酒还在。店主守着的当然不是一瓶酒,是这个地域人和人相互对望的方式。当所有无主的酒水被汇集到盆中,当酒干肉尽曲终人散后,你以为用喝早酒建立起来的这种流淌着温暖和善意的生活结束了吗?当然没有,很多年后,有人可能会写一篇《吃早茶的人》。
相比《喝早酒的人》,《逐水船》在意蕴上更胜一筹。
作品时间跨度很大,水气淋漓的河面,女人的命运几乎与风浪同频,宁静安稳往往只是片刻,更多时候在风浪中挣扎颠簸,就像《活着》里面的富贵,仿佛一天一个活法。作品在不到一万字的篇幅里基本抓住了所有需要讲述的重点,文字简洁投入,心无旁骛,几乎一口气完成了故事的讲述。“逐水船”作为命运的符号意象,也有完整且令人信服的表达。可贵的是,在一次又一次的苦难面前,女人内心却光亮日甚。所谓“一念成佛”,只是这“一念”,绝非凭空而降,没有尝尽世事的悲苦,阅尽人间的暗黑,窥见依稀的光亮,读懂命运的无常,断然不能一直对这个世界抱有期待的希望。
我理想中的好小说,一定要有扎实的文本,精准的语言,宽阔的意境和高妙的表达,它应该一直保有对光和热的期盼,对笔下人物深刻的理解和由衷的尊重。当然这需要作家拥有宽阔、悲悯和庄严的心境心性,更需要作家对人类终极走向做出先知般的预言和判断。
写出理想中的好小说,得先有写好小说的理想。以上两个小说在很多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,但是我们欣喜的看到,青年作家笔下已经有了云蒸霞蔚的气象,字里行间时刻闪烁着的善意和对人心无微不至的体察,比炫目的技术和精致的文本来得更有力量。
青年作家熊生庆一定有写出好小说的理想,也正阔步走在写出理想中的好小说的大道上。
(肖江虹,男,1976年生,贵州修文人。中国作协会员。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。作品发表于《当代》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天涯》《山花》等刊,被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月报》等选载,入选各类选本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小说选刊年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华语青年作家奖、贵州省政府文艺奖等。)